老之将至
中国的人口问题现在只是个开始,未来十年才是爆发。
前几天看见罗玉凤发了一条关于人口红利的微博,一堆人点赞,说她的见识“超过了90%的专家学者”云云。她是这么说的:“经常看到有人在鼓吹人口红利,其实人口红利是资本家的红利,不是人民的红利。劳动力过剩,工作更加难找,工资待遇更低,生活毫无质量可言。”
玉凤姐姐的这段话,没有一个字是对的,就是“一派胡言”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:安徽人大量涌入上海。上海摩肩并踵的都是人,上海平均工资降低了吗?东北人口净流出多年,东北平均工资上升了吗?
做网站的都知道梅特卡夫定理——一个网站的价值等于用户数的平方。为什么是平方呢?因为除了用户数,用户彼此之间的互动为网站创造了另一个维度的价值。自古以来,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城市,人均收入就一直高过乡村。因为人群聚集所产生的贴近性和规模效应,强化了人际间的沟通和交易频次,产生了五花八门的工作机会。从而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。
喝了酒没法开车,只好找代驾。这种一年用不上几次的低频次服务,只能出现在大城市,人口基数多。你去小县城代驾试试呢?小县城里出租车都没有!
小农自然经济的思维是“人少,人均土地就多,打的粮食就多。别人喝玉米面糊糊,我家能吃玉米面饼子”。但是商品经济思维却正相反——有足够大的人口基数,才会有更多交易。小镇杀马特,年轻时开个大摩托,在县上浪来浪去。结婚了,有孩子了,他们去哪儿了?他们卖了摩托,换了辆电瓶车,跑大城市送外卖去了。原因很简单:人越多的地方越能赚更多的钱。
人口的不平均分布,最终会因为捐滴效应,让大城市之外的农民也获益。比方说韩国,是亚洲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人均GDP过3万美元的国家。韩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聚集在首尔。首尔多大呢?只比杭州的一半大一点点。这么点个地方,聚集了2500万人口。成了韩国经济发展强劲的火车头。那么首尔人发财了,钱多了,就有更多的钱用来买农产品,周边的农民也跟着富起来了……
所以,人多并不会因为劳动力供应过剩,而造成收入的下降。相反,会因为贴近性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,以及人口规模效应可以支撑各种各样低频次的生意,增加了工作机会,从而提高了人均收入。在人口总量不变的前提下,人口分布的不均衡,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。
尺寸大的东西,比如城市、国家,往往造成理解困难。我们不妨拿两个小区来举例子:有两个小区都在郊外,公共交通不便。一个小区有100户人家,另一个小区有3000户人家。假如你是个钟点工,你会去哪一个小区找生意?简·雅各布斯在她的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一书中,归纳了成功社区的四个前置条件:
1、步行范围内有10000人口(强调人口的聚集和规模);
2、路要窄,拐弯要多(车速会降下来,路边商铺有生意机会。咱中国人的风水里说“曲则有情”,这里的情,可以理解为人情、讨价还价的交易情景);
3、新老房子都要有(不能全是新房子,这样房租贵,影响商业业态的多样性——大家只能都去开咖啡馆,大饼油条店和自行车修理铺付不起房租);
4、不能只有一个主要的商业功能(比如服装街,白天人山人海,晚上鬼城一个。晚上没人睡觉的地方,就不能叫社区。类似的还有曼哈顿)。
如果以后你们要开个小店,以上四条可以作为选址的参考。非常靠谱!
前几年,搞“城市化”,搞了几年后又改成“城镇化”。那这个城镇化是啥意思啊?是厉以宁主张在四万个镇子上撒胡椒面,搞基建盖工厂,就地消化农村富裕劳动力。这实在是太白痴了,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这样的见识,真是吓人。必须是超大城市圈作为引擎辐射周边才是王道啊!我以为这是常识……
批判玉凤姐姐……这是批哪儿去了?不过既然扯到这个话题,就继续说说吧。
我们说人口,第一就是分布。一定要不均衡,一定要产生大城市中心圈。撒胡椒面肯定不行。那么第二呢,就是人口总量也很重要。不管多大的范围——大到一个洲,小到一个小区。如果人口总数急剧下降,再怎么调节分布也是白搭,无源之水嘛!
古代文明,斯巴达也好,古罗马也好,最后都是亡于青壮男丁人口太少。雅典的梭伦搞改革,甚至把“已婚公民每周与妻子行房不得少于两次,以确保城邦有足够多的继承人”写进法律。而且古雅典人特别可爱,他们和媳妇行房的时候喜欢用后入式,以为这样能就可以让媳妇像狗一样多产。和情妇、妓女做爱,体位才花样百出。饶是这么用心,最终也没解决人口问题。
我们一说欧洲中世纪,就是黑暗黑暗,但是在14世纪黑死病夺走欧洲1/3人口之前,欧洲在封建制度下国泰民安,小日子过得挺好的,一点儿都不黑暗。一下子死了1/3的人,剩下的2/3是不是人均占有土地更多,日子过得更好了呢?恰恰相反——黑死病主要肆虐的是人口密集的城市,城市垮了,农民没有了客户。他们变得更穷了。
除了分布、人口总量这两个因素,我们关注人口,还要看第三个参数——人口的年龄结构。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“60岁以上人口占10%,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%”。我们国家,2018年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是17.9%和11.9%,超过得不是一星半点儿。更糟糕的是,这个数据还会加速恶化。因为,中国人口结构的问题并不是人越来越长寿,而是孩子太少了。2018年,也是中国16岁以下的孩子首次少于60岁以上的老人。全球各国生育率(当年新生儿/总人口)平均数是2.5%,我们国家2017年就已经跌到1.24%了,还不到全球平均数的一半。
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,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。我们可以用以下数据进行推测:
1、我国初婚年龄是27岁左右,也就是说,现在生育主力还是85—95年龄段。在这批人手中,我们国家已经老龄化了,已经16岁以下孩子少于60岁以上老人了。可是95—05这一年龄段的年轻人,数量只有85—95年龄段的60%。也就是说十年后,才是断崖式下降的开始。中国的人口问题现在只是个开始,未来十年才是爆发;
2、欧洲于上世纪90年代,美国于2007年,出现了“已婚+长期同居”人口比例低于50%的情况。也就是说,在欧美,结婚是少数人的选择,不结婚的反而是多数。我国总的数据还没这么邪乎,但是把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单独拎出来看,情况可能比欧美、日本和香港更严重。
在日本,34岁以前从没过婚的男性接近一半,女性超过1/3。香港稍微好一点,但好得并不多。我们大陆还没有这个统计。但是就离/结率(每年一个城市中离婚总对数/结婚总对数)来看,我们头五名城市甚至超过了日本和香港,达到1/3以上。也就是说,这些离婚的,加上从未结婚的,加上丧偶的。中国的大城市和欧美一样——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处于非婚姻状态,大概率是现实。
3、 咱国家的千禧一代(1984—1993年之间出生),不说租房子,就说买房子,已经有7%的买房者明确说不需要厨房了。你很难想象一个连厨房都不要的已婚妇女,会计划生孩子,是不是?
总结一下。我们谈论人口问题,要关注的是三个参数:
1、人口红利不仅指总数的增加,不平衡分布所造成的局部聚集(大城市圈)甚至比人口总数的单纯增加更有利于经济发展;
2、但是人口总数不能断崖式下降,不然扯啥都没用;
3、 除了分布和人口总数,还要看人口的年龄构成。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,就是年轻人不肯生孩子。
说到年轻人不肯生孩子,媒体都归结为大城市虽然挣钱多,但是生活成本高,压力大。生不起孩子云云。这确实是个因素。但现在小地方的穷人,也不肯生孩子啊!所以我觉得,还有另外的原因。其中的两个是:这一代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,又恰逢网络化时代。没有兄弟姐妹,大量时间精力又花在网络上,造成了这一代人普遍的建构人际亲密关系能力的缺失。现在大家都很感慨,平常在网上聊得热火朝天的,真到见了面,反而不知道怎么交谈,哪儿哪儿都别扭。原因在于:通过网络的沟通,我有“随时叫停的选择”,线下的沟通,对面的那个人却时时刻刻占据你的内存,这让人苦恼。年轻人不结婚、不生娃,更可能的原因是:嫌烦。
说半天,老了怎么办呢?这还真是个大麻烦。未富先老。政府肯定指望不上,子女更指望不上——大城市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处于婚姻之外,哪来的子女呢?
我们国家是从1970年开始计划生育的,到1982年甚至把计划生育写进了宪法。这个制度,到2016年才正式废止。46年期间,除了少数民族和极个别情况,全国严格执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。这在人类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。这个执行了两代人时间的独生子女政策,造成了今天中国一个特殊的现象:全国都是421家庭。
一国之公民,生育也要被利维坦“计划”,会造成多么惨痛的后果,我们这一代人,不幸成为亲历者。哈耶克说:“当下发生的事和历史上发生的事,唯一的区别是我们不知道当下发生的事的结果是什么”。今天,计划生育政策终于成为历史,我们也知道了它的结果是什么。但为了这个答案,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惨烈。
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,我们都要看三个层面——政府的、社会的(企业和NGO)和个人的。只有三个层面相互辅助,结果才会比较好。任何全社会尺寸的问题,都不可能仅靠一个层面的力量得到解决。那目前,养老这个事情,政府、企业和个人,做了些什么,又应该做些什么呢?
政府
这么大个祸,就是政府惹出来的。按说应该由政府来解决。不能只管杀不管埋,对不对?更何况当初推广计划生育的时候,还承诺过“只生一个好,政府来养老”。但是现在,就不再提了。别说政府出钱养老了,就是社保,我们只是让政府管着,竟然也亏空得一塌糊涂。那为了填社保基金这个窟窿,势必又要印钱。如此一来,就算你省吃俭用在银行里存钱打算养老用,也会大幅缩水。
因为2016年才停了计划生育,所以关于养老这块,政策和政策配套就比较零碎。用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秘书长曾琦的话说,就是“缺乏顶层设计……政出多门、条块分割、有的甚至互相矛盾”。一句话——现在还处于捣浆糊阶段。
今天,我们国家超过60岁的老人是2.5亿,一半自己住,一半和子女住。民政部门的养老院解决了多少老人呢?3%!护理人员素质极差,都是些没受过教育的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。政府办的养老院差到什么程度?我妈以前一直嘴硬,跟我们说“我老了就去养老院,不受你们的气!”前几年我们家邻居老太太中风,被送到养老院去了。我妈去看她,带了点饼干——独立包装,每块饼干都有个塑料袋包着的那种。去了拿出饼干,邻居老太太抓过来就往嘴里塞,塑料袋都来不及拆。护工显然为了减少她的大小便数量,故意不给她吃饱喝足。把我妈吓坏了,回来就改口了,“我不能动了你们可得管我呀!”再没提过去养老院。
养老院虐待老人的事情,时有耳闻。你想,会学话、天天父母接送的小孩子,幼儿院老师都敢虐,躺在床上不能动、一天比一天糊涂,三个月半年子女不去看一眼的老人,过的能是啥日子?
子女
有一半老人独居,还有一半老人和子女过。那和孩子一起过的老人,是不是就比在养老院的幸福呢?真不好说啊!媳妇虐待起婆婆来,比护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儿媳妇和老婆婆实在是天敌。
选择和子女住在一起,并不是因为这样比较好,而是除此没有别的选择。上一辈子的老人大多没啥钱,又好面子,在外面要维持一个“我家孩子孝顺”的形象。孝顺啥呀?久病床前无孝子啊!家政行业都有了行业潜规则和专属名词了——杀手护工。意思是,请个护工来家,把长期卧床的累赘老人“解决”掉。这个护工来干一天,就能拿到一个月的钱,然后还能以“沾了死人为由”从家属那里拿一笔“解秽金”。《界面》调查过一个被以杀人罪起诉的死亡护工,她出事之前的六个护理对象,也都是在她去护理一周内就死了。这种事,如果没有子女的暗示甚至悬赏,怎么可能?
说到这个,还有另外一种对老人的虐待。就是,假如你是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,老了之后不管病得多重,子女把你往医院ICU里一扔,浑身插满管子,让你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。反正费用全报销。你的任务就是喘气,给子女挣工资,一个月一万多小两万呢……我当医生那会儿,见过在ICU里住了两年多的老人,下病危通知书家属都不带来趟医院的。
企业
政府总是能把“变坏事为好事”。教育搞不好了,产业化;医疗搞不好了,产业化;住房分配搞不好了,产业化……不仅甩了福利的包袱,还通过设置行政壁垒,坐地收门票创收。就像张维迎说的:“全是市场,则没有权力;全是计划经济,则权力无法变现。”一半市场一半行政垄断,则权力与金钱之间的交换方能大行其道。
这些年,只要冒出个新产业机会,看着是块肥肉,一开始都是官办,搞不下去欠了一屁股债,再改ppp,美其名曰向民间资本开放。ppp,就是政府将行政资源变现最直观的形式。养老这一块,现在应该是政府还没想好怎么吃肉,所以离企业登台担任主角,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不过这两年财政这么困难,地方债务危机严重,养老这块直接跳过地方政府举债官办的阶段,直接跳到二年级,或许是更大的可能。
目前针对养老产业的企业行为,五花八门,机器人、远程在线医疗……但最成气候、也最应该成气候的是养老住宅。逻辑上讲,就像我在上一个宝帖里说的,几个亿数量的老年人,一定要集中起来形成贴近性,才能降低护理成本。这种距离的消失,必然要通过养老小区这样的居住形式来解决。
养老住宅顾名思义,它与养老院最大的区别在于:老人在小区里有独立的住宅。一人一个房,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机能的衰退,生活的独立性逐渐丧失,从请护士和护工到家来照料生活和提供简单医疗服务,到最终搬到小区所设置的医疗护理中心。在美国,这个模式被称为CCRC(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)。
但是这种模式的养老住宅,向中国移植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适应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1、中国不像美国,没有靠谱的金融产品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理财收入。人家那种专门服务于退休人员的信托式基金,你就是痴呆了,每月该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,不会差你的。咱中国的老人就不行,就算你脑子和年轻时一样好使,也斗不过狡猾的基金经理。你说那我不投资了,我搁银行吃利息……现在这通货膨胀率,把钱存银行已经完全不靠谱了。
2、房子太贵了,老年人买不起。所以现在有人主张在近郊便宜的地方兴建养老小区,让老人把自己在城里的房子租出去,这就是所谓的以房养老。问题是再过十年八年,城市里的房价是否还能像今天这么坚挺,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事情。
3、越来越多的老人,并无子女。那他们的养老公寓的身后价值,需要在生前就要被提前使用。不能出现活着的时候吃糠咽菜,死了身后留套房子的情况。这就需要与这种养老形态紧密配套的保险产品。现在,正因为国家政策、相应金融和保险产品配套没有跟上,养老住宅还处于房地产商自说自话的阶段。一个“年轻时可投资的产权式养老公寓、老了之后自己去住、渐进式关怀、保险公司将房产价值提现贴现”的基本款产品,还没有出现。
政府靠不住,孩子不能靠。那逻辑上就只剩下两个选项:企业和同龄人彼此依靠。但问题是,我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。
彼此依赖的话,就是互助式养老。这个互助式养老,特殊的困难在于:由老人组成的社区也好,社团也好。其生存能力是逐年下降的。这种建立伊始就决定了其衰败性质的社区或社团,必须不断注入新血液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,才能维持其活力和生存。这就需要规模、机制设计能力,和普适的硬件条件。这就比几个、十几个主妇合伙雇个农民种菜的CSA(社会支持农业)要复杂得多。现在日本也好,中国也好,都出现了几个老朋友共同出资买个乡下的房子、或者在同一幢公寓楼里买房的情况,但这种小规模的、封闭性极强的小社团,随着成员自理能力的逐渐丧失,互助也就沦为一句空话——都不能动了怎么办?最后死的那个人谁来照顾?基于多年友谊的朋友小圈子,如何吸引更年轻的成员加入?
类似美国CCRC的社区,在中国已经出现了。但是因为经验问题,也因为相应金融产品配套没跟上,所以还没成气候。但这必然是未来的方向——以贴近性降低护理成本,是逻辑的必然。但是目前,类似成熟的住宅产品还没有出现,相应的金融保险配套也还没有出现。我们只能等!
不过在等待期间,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,也必须做。就是尽可能多地交朋友。不管我们今后是去官办养老院,还是去养老小区,我们老年生活的质量和尊严,除了钱,还取决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:有没有朋友。在逐渐丧失身体机能和自理能力的过程中,有没有人始终保持对你的关怀和问候,这会成为护理人员对你是否尽心的决定性因素。
抱团取暖,这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了!
(来源:微信公众号“两只母鸡”;文/肉唐僧)
编后记
采编:ZOUDECAO(微信/QQ:82075451) E_mail: zdco@qq.com
感谢作者辛苦原创!部分文章未能与原作者联系,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。转载请注明出处!如果觉得本文对你有启发,可以点击一键转发,分享给我们身边喜欢的朋友。因为分享,所以快乐。
本文来自 德艺志 转载请注明;
本文地址:http://www.zoudecao.net/post/1783.html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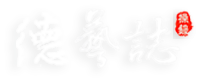 关注设计,提升认知、升级思维和记录生活的博客。
关注设计,提升认知、升级思维和记录生活的博客。